1994
陳凱歌眼底盡是《風月》
1994-10-20
無言無語,無聲無色,愛意油然而生,把他拖進無底深淵,不能自己。在昏瞢的月華下,風,襲人而來,門隙一處溜進了他們的竊竊私語,回蕩在這空房子裡,令他侷促得要命。倏地,緘默的廝守化作內斂的恨愁……隨著心頭一躍一墜,他盤桓在這迤邐的情路上。
戲說《風月》
「安靜!」
庭園中各人把一切靜止下來,室內各人不期然把呼吸聲壓低。本來熱鬧,嘈雜的退思園內外,霎時間鴉雀無聲,就像收音機被突然關掉一樣,寂靜。
「準備!」室內的空氣混和著各入的情緒,凝聚一起。微弱的攝影機啟動聲把時間一下子往後推了七十年,這豪宅隨即時光倒流般回復到二十年代的神采。
無言無語,無聲無色,愛意油然而生,把他拖進無底深淵,不能自己……拍板聲開始了從上海重返這裏的忠良向他親姐秀儀提出歇斯底里的控訴。
|
「我討厭這個地方!我討厭這裡的人……我更討厭你!」一雙憤世的眼睛盯著一雙驚愕的眼睛,仿彿要看著她心中的淚水浸死她自己。沉默。寂靜。
「停!」導演陳凱歌把一切叫回現代,張國榮的演出贏得現場各入的掌聲。
「國榮自己亦覺得今天是他至今在這部戲中演得最好的一部分。」這是陳凱歌後來的話。 |
 |
辛亥革命的一年,少年忠良雙親先後故世,他惟有到江南大戶龐家投靠這世上唯一的至親——姐姐秀儀。失去一切的忠良從開始便對姐姐懷著一種高度純潔的情感,一種無性別無倫常的愛情。然而沉淪於鴉片的姐夫卻一次又一次地在忠良面前與秀儀調情,最後更逼忠良親吻姐姐,令他心碎的是,姐姐竟也積極參與這齣無聊戲劇,一霎間忠良從天上墮入人間,從一個純潔無性別的孩子長成一個男性,懂得了這世上兩性的對峙關係,對姐姐的愛也就破裂了。一日,忠良以砒霜混著仇恨之火替姐姐燃點鴉片煙……
.jpg) |
六年後,上海出現了一個風流倜儻的俊男,他掌握著世上所有女人的心,然而他自己卻被拆白黨的領袖大大掌握著。他,即是忠良,扮演著風月場上的勝利者,用感情敲詐女人的錢財。一次任務迫使他重返龐家,重見的姐姐令他更失望,甚至感到仇恨。大小姐如意是他任務的目標,可他卻料不到如意的反應會如斯熱烈,女人澎湃的熱情竟觸動了他久已遺忘的愛心…… |
放棄計劃回到上海的忠良卻被大大千方百計的在如意面前揭穿他醜陋的一切,大大要粉碎二人之間的感情,誰料卻徹底地把忠良粉碎了。最後,洗盡鉛華的忠良決定重回這家之時,卻竟是如意出嫁之日,他感到這園子埋葬了他一切的希望和愛,他不由再次起了毒殺之心……
「這愛情兩字真的不是好寫的。」
「我就怕這次說得太嚴肅了。」陳凱歌坐著蹺著二郎腿,雙手橫放胸前,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氣魄。聽著他說的話,看著手上的《風月》故事大綱的我是既佩服又為難。佩服的是這四千多宇的故事大綱,要比我先前看過的電影劇本還要來得仔細,故事的發展,人物的關係,心理的描寫,全數有影像地呈現於字裡行間,加上電影開拍前所準備妥當之細緻分場甚至分鏡劇本,無怪乎國內大部分電影在技術及製作條件都落後香港的情況下,卻往往仍遠比港產片拍得精彩,可見一劇之本的重要性。為難的是,以自己的筆力根本不足以把如此詳盡的大綱撮要而保留原來神髓。對故事隻字不提又覺不是,卻又總不可把洋洋四千字都刊登出來吧。力不到而勉為,是迫不得已,只望陳導演看到此稿時見諒。
目下《風月》
龐家一景是蘇州附近,同里古鎮裡的一座光緒年間建築庭院,這裡從前是江南著名水鄉,家家臨水,戶戶通舟,有東方小威尼斯之稱,可惜取景似乎均集中於退思園內,不然必別有一番風味,當然亦需另有一番工本了。
|
到達的一天是中秋節,微雨霏霏,劇組正好忙裡偷閒,休息一天,滿以為可乘此機會找導演一談《風月》,卻被大大小小的會議擋在前面,無法與陳凱歌坐下一談,要找杜可風,他卻也在會議中,張國榮又正好有其他事忙著,我說:「今天不是休息了嗎?」有人答道:「今天不拍攝,能否休息,看你是誰了,我倒沒有見過導演休息,其實這裡差不多每兩星期才停止拍攝一天,他們有太多東西要談了。」
往後兩天的現場觀察中,看到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首先是陳凱歌、張國榮及杜可風的三人組,他們總是聚在一起談,從一對道具花鞋到一場戲的氣氛以至論及全套戲的一切,中間當然夾雜著其他人的意見,尤其是張姓的副導演,然而卻還是他們三人從一而終,白天在現場,晚上在酒店,談過不了,我想大概他們就是整套電影的重心人物吧,導演是靈魂這自然不用說了,可是這些時間之中卻從沒察覺他們手上拿看劇本翻閱的,大家談起來都對每個細節,每句對白如此瞭知指掌,就像在談自己經歷過的事一樣,明顯地各人都各自做了相當充足的準備工夫,態度之認真與投入令人佩服。後來有人告訴我看到導演在翻劇本,我還真的特別跑去一趟呢,卻還早碰不上。 |
|
然後我發覺到每天的拍攝之中,張國榮都在下午二、三時左右便完成他的部分,餘下時間便是拍攝小忠良的戲。詢問旁邊的人,亦表示拍攝以來均大都如此。這種安排,在香港基本上絕對不會發生,無他,製作成本向來也是拍攝間考慮的大前提,所以演員(尤以高片酬的主角)到場拍攝的日子往往是人盡其用。
 |
然而只要稍為想深一層,卻不難明白這安排的用心。能讓主要演員每天專心演一至兩場戲,而用剩餘的半天準備明天的部分,是認真,有要求的製作方式。這背後意味著兩個可能,要嗎,是張國榮願以不限的工作日數而收同一的片酬,要嗎就是徐老板不惜功本。無論是前者或後者相信亦很難出現在香港的製作中。
其次是採訪之多,肯定《風月》及陳凱歌是國內、國外均備受注意的電影及導演,在兩天之間,我碰上了上海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法國的CanaI PIus電視台,據說台灣的採訪隊才剛剛離開了兩天。現場不時見到三、四架攝影機在各忙各的,甚為熱鬧。然而熱鬧歸熱鬧,倒真的辛苦了導演,現場的訪問還算了,早上起床被人拉去拍照,晚間時仍接受訪問,我看見了也替他頭痛。 |
細語《風月》
什麼叫風月?
|
這標題所以是《風月》,就因為這故事正正不是「風月」……不僅僅是「風月」,我不完全抓得緊這個答案,然而看著已經十分疲累,甚至神色顯得有點不耐煩的陳凱歌,我不想追問下去,我寧願先作一個耐心的聆聽者,以從中找自己想要的答案,我可以想像得到他已接受過太多太多的訪問了,而問題偏總是千篇一律,我索性把自己筆記簿合上,丟掉那些已準備好的問題,放下筆記後,當然,大家都似乎輕鬆了一點。 Leslie似乎是郁忠良的最佳選角,其實到底從意念來說,是有郁忠良先還是有Leslie先呢?
「一樣!」是同時出現,平衡發展的?
「對!兩件事也是一件事。」 |
.jpg) |
你曾拍過《黃土地》及《大閱兵》,都是受了一些感動而觸發你開拍的片子,你亦說過拍戲是受到某個故事或人物本身的影響而通過電影去表達自己想說的事。那《風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jpg) |
「這是一部我這樣一個男性導演,怎麼看現代社會上面現成道德規範的兩性關係的戲,這個問題是意識形態外的東西,所以大家都好像不是特別注意,可是對我來說,我覺得特別重要。因為照我的看法,其實人是有雙重性格的,一個是生理性別,一個是心理性別,但是大家基本上是以表面的同一標準去要求別人,男人便被視為男人看待,女人亦如是。其實我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 |
「我選擇了女性是為找一個對手,這部片在感情上最後勝利的其實是女方,她能勇敢地面對自己內心的問題,面對自己說:「我是真有足夠力量去面對自己的愛情」,兩個男主角都做不到這樣。」
 |
大家開始喝杜可風的威士忌,吃果仁,我覺得一個健康社會應容許有一些做白日夢的人。人所以有進步都是因為這些白日夢,先有夢想,後有創造嘛?連夢都沒有的話,還可以做什麼呢?《少年凱歌》一書中看過了陳凱歌令人佩服的文字功力,卻原來文字外,他還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
為什麼是二十年代?你拍的戲好像都頗有些時代背景,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
「我想拍二十年代,大家談起中國都是三十年代,我反而覺得二十年代是大家不大談的一個時間,開始時我對那時上海及這個江南的舊鎮有一點印象,然後經過一段時間把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
飲酒,轉換了一下坐姿。
.jpg)
.jpg)
「其實《風月》就是人的故事嘛!時間不是最大的問題,那時的上海不是跟現在的深圳很像嗎?大部分的人都是從外地來的,大家都在不擇手段地賺錢。人們要談愛和恨的時候,決定於幾個問題:你是誰?你身處哪裡?到底你自己想做些什麼?我不認為多數人會談起愛情這事時會有相同語言,我自己想說一個關於愛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深呼吸。
「我不敢保證這是成功的電影,但會是有意思的電影,我希望可以拍出一些心靈感。只怕這片子太嚴肅了,這是一個真的求根問底的緒論,人類的感情到底是什麼。」
盡是《風月》
跟陳凱歌談話,會使人覺得從他身上越知得多便覺自己越知得少,這包括《風月》,包括電影也包括其他。截稿前道聽途說到一些關於《風月》停拍的消息,希望它的問題能盡快解決吧。這幾天上海之行,令我想起一次杜可風說:「電影是這幾個人,在這段時間,在這個地方所做的一件事。」好一句語中有,語中無的說話,我亦只可以說在九四年的中秋前後,在蘇州附近的吳江市中,這個劇組的人,每天的生活,都盡是「風月」。
電影雙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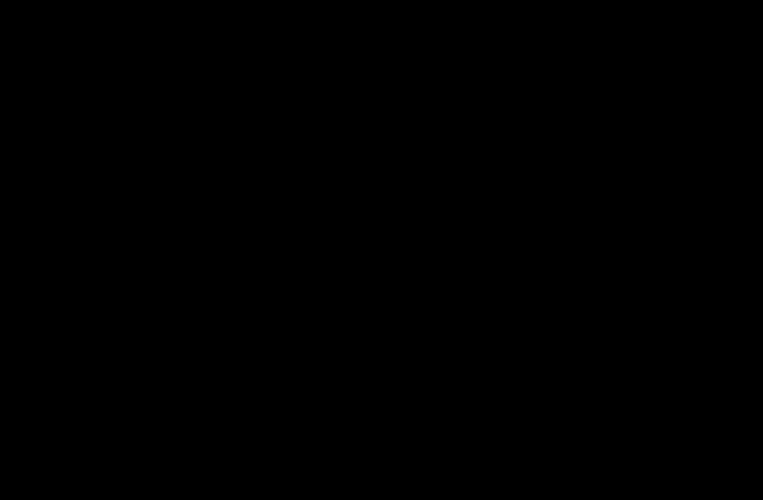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6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6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