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金枝玉葉》虛情假意 欲言又止
文:登徒
看《金枝玉葉》確是百感交集,觀眾反應愈是投入,對那些精心設計的處境愈是笑得厲害,便愈叫人擔心。電影叫人參與的不只是一場嬉戲及幻像,而是表達了對約定俗成根深締固的性別角色,及背後一套頗為保守性觀念的認同,縱使製作人左閃右避,在橋段上搞得有聲有色,對敏感問題左右言他。
陳可辛的【電影人】可算是本地創作人中最敢與性作為禁忌的課題對著幹,這點可從其深受西方電影觀念影響所致,甚至從他電影瀰漫一片中產西化的氣氛,可知把「性」禁忌擺出旗幟鮮明的姿態實其來有因,《風塵三俠》寫男人性壓抑及態度,《晚九朝五》採取個案重演方式,以探討中產年青人性生活的真貌,把一撮人的取向宣諸於電影,這種揭瘡疤的態度,無疑是對應著中國人社會瀰漫一片的保守風氣,尤其港產電影的性從沒真正像樣的位置,由此而引申出一套新的創作態度,敢於把《記得香蕉成熟時》作為成長經歷來處理,而能恰如其份,亦由於此,無論從創作態度及給予觀眾的期望,都有別於王晶的電影,縱使後者更善於經營作為消費品的大眾「性」文化。
但稍為留神於《金枝玉葉》而不是為一串編排得用盡心機的性別錯置的笑料而搞得頭昏腦漲,也可以分辨得出陳從來沒有為同性戀開拓出比以往港產電影有所不同的空間,片中真正的同性戀態度的形象化身,只有曾志偉及羅家英的乸型,一個嬉皮笑臉一個神僧鬼厭,最後被安排成一對,簡直是注定在電影中受揶揄排斥的順理成章結果。
《金》最重要的,並不是張國榮頓悟愛情原來無分男女,而是透過袁詠儀的假鳳虛凰,一次過對性別及偶像作近距離膜拜,這見諸袁拆散了金童玉女,而分別代替女觀眾接近近乎完美的美男張國榮,與及同時間代替男性親近劉嘉玲,故此,當袁的手被劉捉到自己巨大的胸脯前,與及袁說出自己想知道為何劉的胸與自己有天淵之別,這種舉動編排完全是一種性幻想產物,姑勿論是出自男或女,電影便在這種夢幻感中緩緩而進,觀眾更在此等笑料中爆發興高采烈的笑聲,人的情緒愈高漲,証明的是性別的壁壘從來沒有被創作人拆掉,相反,卻是愈築愈高,張國榮最後擁著女裝的袁詠儀,說著「男女都好」,效果之含糊,實是自圓其說,替自己電影政治敏感降溫的措施,內裡看不見真正的同性戀的態度,對尊重選擇的豁達思考,觀眾可以見到的,是一個更近乎天荒夜譚的金童玉女結局。
當然,要求電影承擔一定的社會使命,甚至為社會上長期受到歧視一族平反,本來是多餘及妄想的,香港電影從來沒有這種傳統。《籠民》基本上也是訴諸溫情氾濫,對問題卻從沒有真正出頭的興趣,但問題是,陳把同性戀從衣櫃中抽出來,把它變成主要的橋段,製造大部份的娛樂,甚至把性取向(男女)崩潰賜予電影中的張國榮,卻竟然沒有理直氣壯為這種姿態支撐到底,張的態度便是含糊得簡直使人尷尬,「同性異性的戀情,誰說有本質上分別」竟然不能宣之於口,大方坦白指給觀眾看,同性就只是這麼一回事。
現在出來的效果,不可能被看成藝術手法上的含蓄,而是給太多照顧於觀眾約定俗成的性觀念,創作人又根本以此過橋,以為真正給予同性戀真實而可悽的空間,實是一場誤會。創作人純為橋就橋,最終又再按照市場需求索求結論,尷尬自然少不免。更難堪的是,這樣地把本來極有潛質發揮的社會話題,一次過消費掉,與王晶與大眾化處理有何分別。間或有者,可能是王晶更為坦白,更為忠於自己。把性關係還原到最基本動物需要上,《戀愛的天空》的女同志何嘗不是以此宗旨渡日,男女男男或女女從來都服膺在這規律上。陳打著闖開性禁忌愰子,最終還不是馴服於大眾規律,清楚瞭解社會矛盾所在,利用作為話題,卻處處左閃右避,最終恐怕仍是以票房、笑聲論英雄。同志問題說到底仍是次要,這些基本上並不是在看《金》之前期望得到的,感慨亦因為是出自陳的作品。
退後一步而言,若撇開電影中的露骨的性動作不談,假鳳虛凰的橋段始自陳寶珠蕭芳芳時代,橋段上並不真正有所進步,透過假鳳虛凰的偷偷摸摸,亦是換得相類似的滿足,這種在強調創作人本色的電影中,實不知是過份保守還是懶惰,角色的描寫更是空洞得令人吃驚,張國榮的作曲家,劉的歌星,袁的低下無產階級,從空虛中建構,發展成的只是空殼般的角色,張國榮要回歸平淡更是描寫乏力,比起《錦繡前程》中的林超榮,實無需再言差別。
當然,從觀眾完場後總結出高頻率的笑聲,靚人靚景的視覺滿足,《金》實已立於不敗之地,但對於陳可辛以及電影人,又是否可以多要求一點,而不會被誤為惡意挑剔或吹毛求疵?
1994-08-00
電影雙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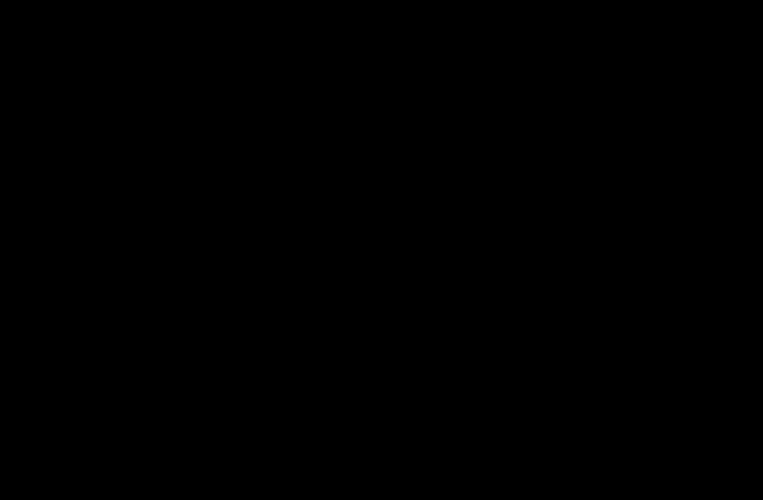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