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由影片《紅色戀人》公映引起的爭議 看大陸電影的生存環境
文:李以莊(廣州)
影片《紅色戀人》及張國榮所飾共產黨人形象觸發之爭議,暴露出大陸當前批評及創作觀念的問題,其意義已超越對影片本身的評論,甚至有人想把反對的呼聲弄大,令有關部門禁映此片,幸而今日之中國已非昔日,儘管說 “NO” 的人不少,但影片照放,不同意見亦可發表,不過據說票房不如理想,不知同爭議有無關係?但這場爭議實在反映了大陸電影的生存環境。值得關心大陸電影市場的朋友關注。
首先,我們只應根據實際作品作評論。可是我們的觀衆甚至影評人,由於長期受某種革命模式影片的訓練與熏陶,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勢,說反映共產黨人的革命生涯,定要如過去同類影片那樣正面表現革命鬥爭,否則便斥之為「不真實」。
批評一:未能正面敍述革命鬥爭
《紅》片故事是:由美國醫生佩恩回憶他年輕時鍾情的中國女孩和她那假扮「丈夫」的革命者,一段驚心動魄的歷程,其間內蘊的高尚情操與人格魅力,令他終生難忘。這視點,決定了本片不能正面敍述革命鬥爭,作為局外人,佩恩的回憶只能是他所知的秋及靳的感情生活。這視點不但關乎內容,也決定了表現手段。片中佩恩奔往上海大飯店時,路上和飯店大堂,均空無一人,這是佩恩的主觀鏡頭,且有強烈感情色彩;亦體現了本片的風格:著重於展示人物的內心感情。指責影片不表現革命者生活的主要區域戰場,實在對錯焦點,導致批評的錯位和無的放矢,批評者陷入主觀臆斷。這種輿論無助於藝術家展開想像的翅膀,也易於令創作陷入公式化。
批評二:有人性沒有黨性
試想,中國革命戰爭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與事迹,但幾十年來,反映戰爭的影片老是那幾個模式:如表現領袖的戰略思想,於是軍事會議、大地圖、行軍、戰鬥場面;還有支援前線的老百姓,且必定有一個代表人民的老大娘,又或表現人民戰爭,便是地雷戰、地道戰......。前蘇聯的衛國戰爭只有幾年,但他們可以有《黑耳朵白比姆》、《這裡黎明靜悄悄......》這樣的影片。荷里活的賣座片《雷霆救兵》,竟表現美軍司令部為安慰一位為戰爭犧牲了三個兒子的母親,派出八個兵去敵後救出她最後一個兒子。因為戰爭是千百萬人參加的,關乎每一個參加者個人的命運、家的命運、國的命運,有衆多視點和題材,而革命題材也可以有多個視點和個人命運的開掘。現在竟有人指責張國榮飾演的共產黨員,只有「人性」,沒有「黨性」。不知道這位先生是否認為共産主義理想同人性是對立的呢?
批評三:不表現地下黨人的革命活動
又有人指責影片完全不表現靳的革命活動。其實影片也有表現,只不過僅是佩恩所能看見的罷了。靳約見佩恩,希望這位常在報刊寫專欄的外國人能寫點關於長征的消息,以便衝破國民黨封鎖,讓世界知道紅軍近況。靳特地在鋪開地圖的空屋同他秘密見面,並告以紅軍長征到何處,駁斥了說紅軍被消滅的謠言。這是佩恩所能看到的靳的革命活動。片中佩恩獨自在空屋走動的鏡頭,不單表現佩恩對他們神秘生活的追尋,也呈現了靳與秋作為革命者所過飄泊不定、充滿危險的生活。靳作這會面,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是冒了性命危險的。但他能想到國際輿論,且敢冒此險,表現了他作為職業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敏感與膽識。
這部影片把表現革命前輩的感情生活作為主要內容,而將革命活動推向後景,為什麼不能允許這種視點的選擇?甚至視為罪莫大焉?!導演是在為影片《紅櫻桃》收集資料時聽到革命前輩講述他們的愛情生活,深受感動而産生創作衝動的。影片亦確實展示了當年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令今日物質生活相當豐富的當代觀衆,在精神上得到昇華。生活固然多姿多彩,文藝對生活的反映,亦有各種角度。藝術家有權選擇他感受最強烈的視點切入並據此展示生活。我以為藝術家這種權利是神聖的,對自己所反映生活的全情投入乃至迷戀,是藝術作品成功的重要前提。
批評四:缺乏地下共產黨員的共性
關於共產黨人的形象問題,靳的形象爭議最大,不少人認為靳不具備常見標準型地下共產黨員的共性,甚至說他只是一個「情聖」。這令我想起恩格斯讀了明娜考茨基的小說《舊與新》後對她的批評:在主人公阿爾諾德身上,個性「完全消溶到原則裡去了」。接著,恩格斯說出了他的名言:「每個人是典型,然而同時又是明確的個性,正如黑格爾老人所說的『這一個』。而且應當是這個樣子。」「這一個」既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共性寓於個性而存在。如果只有共性(甚至誤解典型即共性),只能是符號與模式。
鮮明的個性才是人物鮮活的表徵。靳的形象最動人之處在他的人格魅力及他對信仰的執著。在邀請荷里活編劇來合作時,導演曾擔心雙方意識形態方面會有許多差異,但實際上不是這樣。他深有感受地說:「實際是不管你信仰的是什麼主義,不管這個主義的內容是什麼,這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變成一種人格的東西,一種個人的東西。追逐理想追逐信仰在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是值得崇尚的。」
早期共產黨領袖如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都有很高文化素養。導演說,他心裡的共產黨員是「具有深厚修養的人」,「堅定和頑強,是在於他的內涵」;不在外表的五大三粗。靳的形象確是過去作品中所無:出身富裕家庭,充滿浪漫氣質的文學青年,在法國留學時,愛上學音樂的安霞,並因其影響而參加革命。靳正是經由這獨特的歷程,成長為經受了長征考驗的紅軍指揮員,這是他成為「這一個」形象所獨有的。共產黨員首先是活人,人的個性千差萬別。我們的批評不能同希臘神話中那個外號「鐵床匪」的強盜那樣,把任何人放到他的床上,長了要砍短,短了要拉長,直至把人弄死。
我接觸過許多革命前輩,經歷、素養、個性極不同,不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餅。且並非「完美無缺」。導演說,很多片子在表現共產黨人時,「就是英雄事事跡」,他卻「要對感情問題進入到個人化的表現」:表現人格的魅力。我以為影片達到了他的追求。展現了那個時代革命者對信仰的執著和置生死於度外的崇高境界。
就此而言,影片有突破框框的創新意義。其自我超越勇氣與開拓精神獲肯定。著名演員張瑞芳說:「我是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張國榮演的靳我能接受。」曾任《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演地下黨員李俠的孫道臨說:「張國榮演的靳與我演的不一樣,但同樣是地下黨人的形象。」評得中肯!有人說,靳只是一個學生領袖型人物,說這種人是上不去的。但歷史事實是:早期共產黨的領袖,均是知識份子,有深厚修養。共產黨恰恰是由這樣一批並非因爲家中沒有飯吃才參加革命,相反是因為能夠讀書,甚至留洋,因而有可能接觸和進而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創立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由工農自發産生的。至於革命者個人命運,是另一範疇的事。
批評五:自願被捕不符合黨的紀律
關於時代背景問題,靳最受攻擊的行為,是他拿自己生命換取秋秋母子性命,甚至有人把靳「拼命營救戰友」行為,斥為「自願被捕,交換戀人」,「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行徑。又無視影片劇情規定,硬說靳領導著上海地下黨組織,其實影片已交代:靳是到上海治病的,不在上海地下黨戰鬥序列中。特別是他所負戰傷,隨時會暴露他的紅軍身份。按地下工作紀律,他不應也不會同上海地下黨發生橫向組織關係。組織上給他派了能說英語的革命青年秋秋,假扮夫妻陪伴和照顧他,在租界找外國醫院為靳秘密治傷,她很好完成了任務。秋秋崇拜愛慕靳,靳發病時,秋秋為減輕他的痛苦甚麼也願做。但她在事後的留言中,向靳表達了她的愛,說明在他昏迷時發生的事,表白她渴望在他清醒時也能同他廝守。這愛情的產生,乃人之常情。地下環境中,實不乏假夫妻弄假成真的例子。可惜靳讀到此信時,秋秋已被捕,情況非常危急。
我們設身處地替靳想一想:他摯愛的妻曾為掩護他,在他眼前跳樓死了。現在,秋秋又因給他買藥被捕。靳無法承受兩位摯愛親人為他犧牲的殘酷打擊。秋當衆奪槍殺了當警察局長的父親,粉碎其破壞革命的陰謀;又在法庭上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她首先是一個革命者。作為她的戰友,靳決不能坐視秋秋被害,於公於私,他都必然要拼全力營救!
地下黨組織是單線領導,不能發生橫向聯繫,地下黨員有時要各自為戰。不同於作為執政黨的中共那樣的組織系統及辦事規則,也不應作此誤解,當時,靳能做的便是利用佩恩所享有的外國人特權。由他在租界巡捕房當差的英國朋友克拉克出面,代表租界監獄將靳交換給國民黨監獄,換得秋母子性命。國民黨的目標是靳,因此交換得以實行。對此,導演曾作調查:1936年上海在押政治犯分別押於國民黨監獄及租界監獄。故有此空子可鑽,今天我們在批評靳之前,能否先對史實有一點認知呢?
不錯,地下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不能自投羅網。但黨的紀律根本是為了保衛黨的利益,黨的利益不是抽象的,包括如秋秋這樣具體黨員的生命安危。試想,靳既不能與上海地下黨聯繫,他發現戰友因照顧自己而被捕時,他應怎樣辦?導演亦曾反問指責靳去營救秋秋的人:「你說他該怎麼辦?」靳重病在身,隨時會死;秋則正年輕,並已證明是好黨員,即使從保全革命力量考慮,也是值得的,何況是—命換二命呢?導演將他就刑與秋秋臨盆的場景及槍聲與啼聲,用平行蒙太奇交叉剪接,寓示革命者生命的延續。有人認為靳被捕,會導致黨組織破壞。且不說靳當時是單兵作戰。回顧中共歷史,雖有過總書記被捕投敵事,卻非所有領導人被捕都必然投敵那樣宿命,被捕不等於必定叛變,錚錚鐵骨者方志敏、瞿秋白即是!靳邁出那一步,是去赴死,不是為了偷生!
影評人不以影片實際出發,只作人身攻擊
古人對創作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期許,惜因長期思想禁錮,我們的文藝創作卻走不出「定勢」。本片導演力圖創新,有意開拓建國以來很少觸及的領域。在選演員時,他也按自己不同一般的認識去作選擇:他選擇具有知識份子浪漫氣質的張國榮飾共產黨員,而選形象粗獷且演慣英雄的陶澤如飾叛徒,導演說難道叛徒就—定是小白臉麼?當然,觀衆可以不贊成導演的選擇,但也只能從影片的實際出發,指出這種選擇錯在何處,卻不能斥責這選擇本身。如有人斷言選張國榮飾共產黨人,便是想迎合美國人,或是純商業炒作。卻不從影片所呈現的實際去作令人信服的批評。
我原先便曾擔心張國榮不能演好這一角色,但影片的實際卻證明張的演出成功,他的氣質符合角色。對導演的創新勇氣我充滿敬意。我特別不能接受一些人甚至對張國榮進行人身攻擊,羅列他過去演過的同性戀者、阿飛等角色,把他們代入為演員本人,再加以挖苦。又有人不作調查,便斷言導演找荷里活的編劇幫忙打磨劇本,是為了取得商業利益,製造「三分鐘一噱頭,五分鐘一高潮」,卻不指出影片中何處有這些毛病。
其實導演弄這部影片的劇本已有三年多,請荷里活編劇的原因,是因片中一個主要人物是美國人,請他們幫助按美國人的思想與行為邏輯,把這個人物塑造得可信。我以為這做法是必要的,如今影片中佩恩的形象非常有光彩。監製告訴我,荷里活的編劇除另外對劇本的節奏提了一些意見外,並沒有改變劇本的結構及人物關係。早有人預言,《紅色戀人》既「以全新視角演繹中共地下黨人生活」,定成靶子,必有子彈拜訪。不幸而言中,願創新者能前仆後繼,不斷超越,藝術創作或能爭得一片自由翺翔天空!但能否也將槍口對著那些粗暴批評呢?!
期望多點理解寬容,為大陸電影創造更寬鬆的生存環境
正因創新者處境嚴峻,影片敍說事件時,對背景能交代得更清楚,或可避免不瞭解歷史的年青人産生誤解。但如果觀衆虛懷以待,不存先見,還是可以看懂的。導演聽說一些人有那麼多的誤解時,曾說了一句令我感慨不已的話,他說:「我很同情這些人!」
魯迅曾把作者與批評家關係比作廚司和食客。指出:「批評的失了威力,由於「亂」甚而致於「亂」到和事實相反,……」我想若廚司做一碟炒蝦仁,食客可批評他炒得是否滑嫩,卻不應指責這蝦怎麼沒有從事戰鬥所必需的硬殼及硬嘴?甚而斷定這不是蝦?
其他藝術可以等待未來人的理解,電影卻必需獲得當代人的喜愛,才能生存下去,因為電影耗資巨大,如果它不能最少收回投入的資金,它便無法存活。在此情況下,作為「上帝」的觀衆的理解與支援,是生死攸關的。魯迅曾說:要有天才,須先有適於天才誕生的泥土。影評人在營造這種土壤方面,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讓我們對中國電影藝術家多一點理解與寬容,為大陸電影的繁榮創造一個寬鬆的生存環境罷!
1999-12-00
電影雙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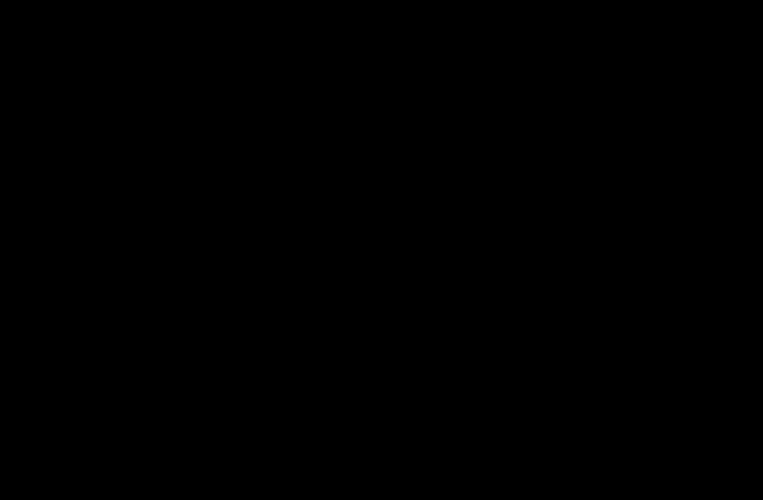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