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風風月月
陳凱歌在《風月》一片中,展現了一對男女峰迴路轉的感情轇輵,在情愛類型片的範疇中做了一個跡近完美的示範作,同時亦為其電影歷程中的探索時期,正式劃上一個句號,在他揮出這個蒼涼的告別手勢同時,其獨特風格亦終告滑落。原屬於陳的零碎但獨特的知識分子式的觸角已全然隱去,代之而起的是完整但並不獨特的通俗敍事技巧。
但通俗並不是罪過,問題是在創作者道盡風月故事之後,觀者猶未能感到一絲涼薄之意,反而若有所失。另一方面,陳在求變的過程中傾向朝著另一位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的路子走去,但在陳重複著張數年前的老路時,張早已像脫手狡兔,跳升至較高層次。而陳在《風月》中的表現,則教人感歎,他在藝術領域上,還能走多高多遠。
曾幾何時,中國第五代導演手中像握住了能開啟時代大門的鑰匙,數度貫穿了中國文化的迷思,令原本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古國歷史脈絡像給解了碼般,還原為一幅幅有跡可尋的圖像,對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夾縫的中國人的悲劇,作出了可被理解的詮釋。這對於一向看慣了沉澱著一片感傷情懷的第四代傷痕電影的觀眾,無疑是帶來極強的震撼。
陳凱歌與張藝謀這兩位第五代導演群中的一時瑜亮,各自在不同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藝術風格。陳在黃土地上,借用比《白毛女》更要樣板化的人物造型與際遇,除去對革命同志歌功頌德式的處理,滲之以黃河為象徵的個人力量不足以抗衡的天命與歷史洪流感覺,成功地將一個陳舊故事借屍還魂為一部解構歷史悲劇的電影。
而張則在處女作《紅高梁》中,擷取莫言原著中的魔幻寫實色彩,既突出人物的傳奇性和可觀性,又將民族世代生生不息的強頑力量彰顯出來。
概括兩者初期的風格,陳其後在《大閱兵》和《孩子王》仍富於知識分子式的的沉思與凝望視點,愛探討民族何去何從的大問題。而張則善於表現,無論是《菊豆》的封建世界,或《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宮幃政治角力,在張的鏡頭底下,都化為眩目的色彩與光影。張精於把抽象的諷喻影象化,即使是陳腐的文學比喻,他都能以簡約有力的筆觸不多不少地表現出來,達到婦孺都能理解,而令在之前已認識這個諷喻的人也不覺老套的地步。
張的技法日趨圓熟,在《搖啊搖,搖外婆橋》,他透過一男孩在七日內的遭遇,將充滿人性醜惡的黑邪世界呈現為古今皆然的殺戮戰場。
反觀陳凱歌,則自《邊走邊唱》開始,已見他遊走於述懷與敘事兩條路線之間的端倪。他當時猶未揚棄,其獨有的沉思色彩,在個別場景中,極力擺出一副深諳通俗的功架。
《霸王別姬》則是他完全服膺於通俗故事框架的第一部力作。
《風月》是另一個充滿異色的故事,在青春期受到乖悖倫常的姐夫及姐姐性侵犯的美少年忠良,不堪蹂躪,憤而毒害姐夫,他出走後在上海遇上黑道大哥大大提攜,成為專門勾引與敲詐豪門婦女的小白臉,並逐漸失去愛的能力,錯失了一段深愛他的大戶小姐如意的姻緣。最後毒害的悲劇再次在如意身上發生,忠良則被如意家族的人殺掉。
導演在營造這樣一個悲劇時,用上了大量人物心理狀態的搖鏡,務求把人物的心底慾望與掙扎表現出來。而《風月》每場戲的設計也的確巧奪天工,杜可風的攝影也的確賞心悅目。但問題是,陳過分倚重技巧,而少了對故事內容作通盤的考慮,容易變得東拉西扯,而削弱了應有的凝聚力。
陳在《風月》的缺點已非把時代改在次要位置這種欲加之罪,而是過份迷戀個人情結與偏執心理,令劇中人物個人心理空間無限脹大成尾大不掉局面。大大兩次大喊「忠良廢了」,端午在上海強暴如意、忠良姐姐在忠良帶走如意後變得失常等等篇幅即使不是多餘,也應該以更精錬的筆觸去表達。反而導演在兩位愛情摔角手在真正「埋牙」肉搏時卻輕輕帶過,沒有將男歡女愛中的狠辣本色表現出來。
此外,陳在《風月》中雖裝作對人物心態瞭如指掌,但其實對很多重要的利害情慾關係仍未能理清。忠良既然冷漠無情,為何獨對大大忠心不二?如意既深愛忠良,為何會忽然對他棄如蔽履?龐家大族父老在之前痛罵端午維護如意,為何仍舉之為一族之長?
忠良在片末被人不動聲色地搶殺掉,如意被忠良毒害,端午登上當家寶座,三個終局哪個也沒有引來很大的悲慟,是因為這是經過佈局的安排,而並非呼應著一種不可逆轉的力量。因此《風月》也只是一連串動作,而不成舞蹈。
1996-06-00
電影雙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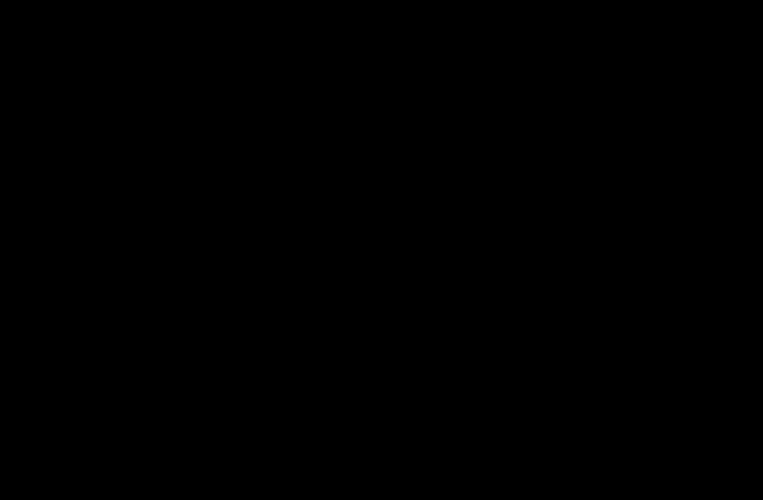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