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張國榮說:愛情有殺傷力
1994-12
文:李元
這是一次朋友間的談心,談得很長,很敞、很深、很動情……
|
深秋一個陰狸的黃昏,在江南古鎮一座光緒年間建造的大園裏,我見到了張國榮。他正全神貫注地聽陳凱歌說《風月》的第47場戲。退思院的後院灰牆上,四個籮筐大的字「鸚鵡春深」赫然在目。院裏擺著大約百來盆從蘇州運來的盆景,蘆杆邊的天幕遮得光影班駁似明似暗。不一會兒,張國榮穿一身民國年代的洋學生裝,架一副小圓墨鏡,提只小皮箱,悠悠的順鵝卵石鋪的小路踱過來。
來此之前,同行中有人說張國榮可不是個容易接近的明星,此行不一定如願以償。湯臣影業公司的製片經理孫慧傳也擔心這些天張國榮很累,打從安徽拍戲,他就不適應內地的氣溫、水質,還老鬧腸胃病,只好見機行事安排訪談。她帶《電影故事》編輯部的趙榮和我,上了一座涼亭。只見張國榮身件汗背心,一條絲綢大褲衩,登一雙圓口黑布鞋,一身像是戲班子練功的裝扮。
「張先生,您一頭長髮不見了。」趙榮笑著說。 |
 |
「是啊,你們好奇怪是不?拍《東邪西毒》一年多了,鬍子拉喳,長髮披肩,人家說我一副吊兒郎當相,現在一下子乾淨起來,反看不順眼啦。」他快活的大笑。
「李元,看來今天運氣好。國榮難得有興致的。在這兒,他說話一直很少,做事可很塌實,空下來就跟凱歌琢磨戲份。」孫慧傳說。
 |
好吧,張先生,那我們就從你跟陳凱歌的友誼說起,你們倆,一位是大陸名導,一位是香港大牌明星,兩個男人有這麼深的友誼,倒真難得。
「是的,我跟凱歌交情很深,是男人跟男人之間那種很純的友情。我倆都不是愛囉嗦的人,平常很少見面,連電話也不通,可是一見面就非常親密,什麼都談,拍片啦,感情上碰到的一些事啦,什麼都聊。平時兩人儘管不多說一句話,但互相非常理解。你知道,我喜歡直爽的人,討厭虛偽的人。我們倆個都很爽,一看就能見底的,所以很投合。」
「拍《霸王別姬》他找我演程蝶衣,他最喜歡的演員是我,真的。(他說的那麼認真,引得我們全笑起來)後來凱歌參加奧斯卡電影節之前,在香港跟我碰面,他說『下一步片子還是我倆合作』。《風月》這片子起先是為我設計的。我覺得男主角郁忠良對於我來說,是目前為止最深最難的一個角色。」 |
你覺得在《風月》裏扮拆白黨郁忠良,跟《霸王別姬》裏的程蝶衣有什麼不同?或者說這兩個男人對待愛情有什麼差異?
「這兩個角色絕對不一樣。我跟凱歌也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從對待愛情的角度來說,程蝶衣是個非常主動的人,他敢愛敢恨。在舞臺上他是個角兒,演的感情激昂,很投入。在私人感情上他從來沒放棄過,可以說是在所不惜的那種男人。」
「但是現在這部戲裏的郁忠良,絕對是個被動者。他做的許多事,滿以為自己能成功,可結果都失敗了,環境造成他是個無奈的人。郁忠良才真正是個悲劇人物,他不敢面對愛,愛是他的一塊心病。程蝶衣卻為了愛主動的豁出去的姿態。這是兩個對待愛情極端反差的男人,這也是我理解角色的一把鑰匙。」
你怎麼理解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呢?尤其在銀幕上非常難表現人類這兩種不同的情感。(孫慧傳一直很興奮的參加這些話題,這時她情不自禁的說:「這問題太有趣,太深奧,我們可以談一個晚上。我跟國榮常常聊起的。」)
「是的,我跟阿傳談過很多次。一個演員要表演到家,歸根結底要懂得人,懂得人性、人情、人心和人欲。在我看來。感情是一種很溫馨的、寬容的東西,燒起來溫度不會太高的。可愛情卻是一刹那的火花,是撞擊出來的一種激情,它是燃燒的,溫度很高,所以有殺傷力。」
「兩個人很投合,心靈有碰撞,心跳會很快,這時就產生火花。這一瞬間激情噴發過去後,愛就轉入一種持久的、溫度適中的感情。我的理解是,愛是短暫的迸發噴射的火花,必須要有相互作用,否則他不會持續撞擊下去。一旦沒有新的碰撞,火花就不會再冒了。有的夫妻結婚後三、五年之後,大家平靜下,激情過去了,感情卻保持得很好,這是一種慣性。可有的就保持得不好,到那時不要說愛,連一般感情也淡了。人們老喜歡問這麼一句話,歌裏也唱到這一句:『你還記不記得……』(他即興唱了起來)其實問『記得嗎?』,就已經是淡忘了,現在不如從前了。愛情和感情之間的區別太微妙了,有很多種轉換方式,我經常琢磨,努力在銀幕上去捕捉。」
你對人類的情感這麼有探究,那你在《風月》中是怎麼將其表現得絲絲入扣?
 |
「我的感覺是《風月》這部戲人物的感情是含量比別的戲要多,至少跟《霸王別姬》不一樣。《霸》片的歷史跨度大,穿插很多事件,比較重外部環境的演變和鋪陳。鏡頭運動是悠悠的,比較平。表現人物感情的起伏時,鏡頭的運動速度較慢,有時會給人一種人物陷於事件的感覺。可是《風月》不一樣,人物突現歷史事件之上,淡化外部環境,突出內心情緒,鏡頭運動激烈,前後反差大。就拿我演的郁忠良來說,特寫鏡頭特別多。我覺得鏡頭運動這麼多,這在凱歌是一個突破,而且國內沒一個導演拍過這樣的戲。往往一個鏡頭包含許多感情層次,差不多幾秒種裏就要表達出稍縱即逝的感情。在三十秒中的鏡頭裏,得有四、五中振盪起伏的感情。從震驚到痛苦、悔恨,繼而憤憤不平;從亢奮到頹喪;從滿懷希望到萬念俱灰……有時候你根本來不及表演出來,膠片就跑掉了。這種時候我總是非常後悔,非常遺憾,責罵自己:『完蛋了!』只好重新拍過。我這個人很死心,非要把所有包含的感情層次一一都琢磨到,在規定的時間裏恰倒好處的表演完。這真像做一項非常精密的高科技試驗。凱歌也一樣,他拍這部片子比拍《霸王別姬》時目標定的更高,他是個追求高標準的人。你剛才不看到他拍了?沒拍到自己心裏定的位置,他怎麼也不舒服。所以有時一個鏡頭得拍很多次,一天下來付出很多,覺得心力交瘁。」 |
「在蘇州(指同里鎮)一個半月得拍完三十場戲,一場有15-20個鏡頭,一天有時也拍不了7、8個鏡頭,一場戲有時要拍上三天。凱歌拍戲起先很慢,像熱身賽一樣,等演員慢慢進了戲,有了到位的感覺,就加快馬力。他總是先拍我的戲,讓一些主要演員到現場來看,給新來的上課。我是習慣不帶劇本到現場,前一天就把臺詞背熟,人物感情琢磨透了,全裝在心裏,我做這份功課是特別用心的。」
你對舊上海的拆白黨是怎麼瞭解的,看了很多資料?
「是的,還看了很多三十年代舊上海的電影。再說我特別喜歡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喜歡到和平飯店去坐坐,喝喝茶。那裏給我一個很舒適的感覺,讓我在恍惚中覺得自己就是這兒生這兒長的上海人。」(孫慧傳:國榮喜歡發發幽谷之情。)
說到幽谷之情,你現在這部片子倒挺有舊時代的味道,那你怎麼讓現代觀眾喜歡和接受呢?尤其是那些就是年代的觀眾?
|
「這問題問的很深。我跟凱歌達到一個共識,那就是影片得有那個年代的感覺,景物也追求很嚴格的時代感。但不能完全照搬二、三十年代,尤其是角色的塑造,要追求一種現代人能理解的認同感。這種既有年代感又有現代感的做法,有時新舊界限很清晰,有時會將時代弄模糊,是一個很辨證的問題,恐怕也是當今國際上很多巨片——文藝片、傳記片都在探索的問題。因為你面對的是一群九十年代的觀眾。你處處死扣,演的拘泥呆板,死氣沉沉,誰還有興趣看?古往今來,哪朝哪代都有愛恨這回事。你要追求一種認同感,只要你逼真的表現了屬於人類的真感情,現代觀眾會以為是真的,他相信你,就是有了認同感。所以不要追求表面化的時代感。我演《胭脂扣》也這樣,演《霸王別姬》也這樣,我追求和琢磨的都是人物內心那份實實在在的感情,這東西是自古以來存在下去的。」(張國榮已經被人催了幾次,端上桌的那份專給他做的香菇蒸雞已經冷了。他熱情的給我們每人分一份,自己滿口嚼著,興致勃勃地等我問下一個問題。我被他那種坦誠、甚至是很童真的熱情感動了。) |
 |
你演過的那些男人,不管是古是今,總有一種出世脫俗之感。你不像那些「陽剛」男人,卻很柔美細膩,給人一種夢幻感覺,你是否有意追求這種藝術風格?
「什麼我不『陽剛』,嗯?你看我挺壯實的,肌肉挺發達的!」(他屈起手臂,挺起胸來,惹得孫慧傳哈哈大笑,說:「國榮可男子氣呢,就是更優雅些。」)
「對了,你說我給人夢的感覺,我所有的賣座片都給人一種似夢非夢的感覺。除了你,還有好些人說過這話。我是有意的,努力去追求這種境界。其實這也決定於我的人生觀。我常常覺得人生在世其實就像場夢,或者說人生很艱難,但人應該有理想,有追求,又超世之念,而這一切只能寄託在夢裏。作夢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刺激的、興奮人的好事,而電影可以給人一種夢的幻覺。」
「我演過很多世俗片,那裏面的角色也是凡夫俗子,有的還真很流氣。不過說心裏話,我是亦步亦趨慢慢形成自己風格的。現在我覺得自己最適合的還是那些高層次的、上流社會的人物,比較貴族氣的。你看今年我主演的兩部片子《金枝玉葉》和《錦繡前程》票房都站在很前頭,但我扮的兩個角色,一個中下層的,一個是高檔次的,自己演下來覺得差別很大。當然我演的大多數是現代都市人,都富有現代人的特點。」
你覺得現代人的特點是什麼?
「我覺得現代人的特點是老不安穩,或是老不滿足,老在尋找什麼。有的人很瘋,有的人愛哭愛笑,有的人呢,閑的無聊時總想找什麼衝擊一下。」
「我自己就是個不甘安穩的人。拍片時忙的累垮了,一休息下來,跟朋友聚聚、打打球、玩玩麻將,再到溫哥華自己的寓所去休息一下,可絕對呆不了兩個月,只一個多月,我就一定回來了。心裏老像惦記著什麼,就又回來忙忙碌碌了。我自己有個愛好,就是喜歡弄房子,每隔一、兩年得換所房子,換個新鮮環境。我買下一所房子,挺有興趣的設計好,自己畫設計圖,自己挑選傢俱,覺得很過癮,好不容易弄好了。過兩年我又覺得膩了,由重新去看房子,搞設計圖,哎呀,真煩死了。你看,我就拗不過自己這本性。什麼本性?也許是喜歡新鮮刺激,喜新厭舊是不?人一直在尋找,永遠不滿足,又老找不到,有種飄飄然的似夢非夢的感覺。我在自己塑造的現代人角色裏常常寄託了自己這種人生解釋。」
「有的人表面上安於現狀,其實那是環境制約了他,是他覺得夢實現不了,是假的,就採取得過且過的人生態度,可是一旦條件有了,他也會『活』過來,生氣勃勃地去找呀找的。人總想改變自己,總喜歡好東西、新東西的。」
要是您不拍戲,我們就一直聊下去。
「真的,我覺得這次來,自己就不是個香港人,而是大陸人。從上次拍《霸王別姬》就這麼以為了。也許我的廣東口音少些,國語純些吧,也許我對中華民族故土很眷戀。真的,你們也當我是大陸人?」
當然,不僅是大陸人,還是個地地道道的「阿拉上海人」!
電影故事(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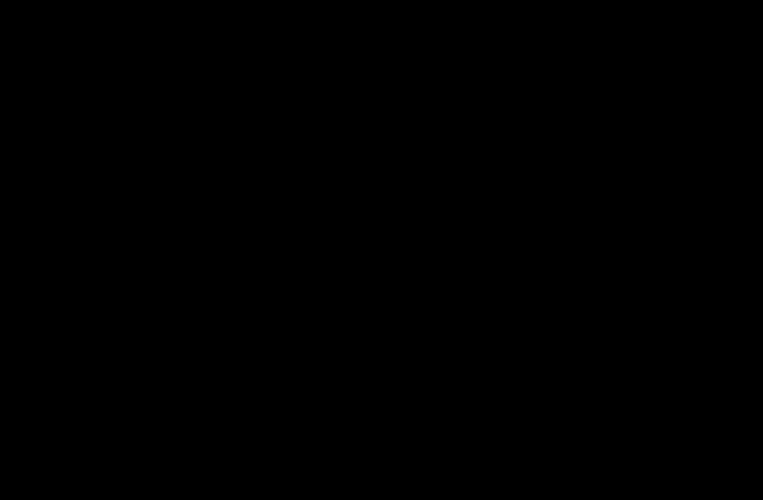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5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5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