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假如我是「鬼佬」
文:阿呆
《風月》有著華美的背景、悽美的戀情,作為一個華人觀眾,看後竟有一種提不著邊際的情意,甚至有種不自然的陌生,但是……
假如我是「鬼佬」,我會覺得陳凱歌的《風月》拍得很精彩。我可以看到中國中產家庭一連串畸戀——姊弟戀、主僕戀及並不真摯的忘年戀等;而在悽美昏黃的環境下,烘托出這些戀情既神秘也迷離。而整套電影中那種逃避與追逐,透過杜可風搖動的鏡頭,把《重慶森林》的意景扭到了中國平房的走廊上,這是代表一種不定、不安又或是尋找的戀局?香港觀眾已「耳熟能詳」,但假如我是「鬼佬」,便會看至眉飛色舞。
假如我是「鬼佬」,我會很喜歡忠良的角色,他似是民初版《阿飛正傳》中的旭仔,不羈而玩弄感情,自我卻又迷失自己;他也似《胭脂扣》中的十二少,風流倜儻但害怕被拋棄。這種外似堅強,內卻脆弱的骨子,張國榮演繹得爐火純青,憂鬱的眼神載著了看不通的思想,而他眼裡看見喜歡的,便可令到她也去喜歡自己,是一種無形的操控或是實際的推銷,可以在如意裡看得一清二楚。
張國榮的忠良,代表著一個在傳統生活中反叛的心;但是,這不成熟的反叛,卻包含了無數的弱點,為何反叛、為何開始、為何結束,他也不是太清楚,所以他一直的拒絕回答所有愛人的同一個問題:「你愛我嗎?」。其實他心中有答案也好,沒有答案也好,最悲哀的是他不懂及不敢去回答,他的生存、他的不羈,就似是逃避這一連串的問題而豐富起來;最後,愛人為他跳樓自盡,彷彿就是不再提供任何機會給他去逃避,而沒有逃避機會的忠良,在那時就如一隻沒有腳的鳥(阿飛語),軟弱無力得跪了下來,待他可以提起勇氣說句:「我愛你」時,自己已被棄置在過去的夢境中——原來在中國人中那種不羈是這麼人性,比起荷里活那種大奸大惡,印象鮮明的角色,這實在「深層」了不少。
假如我是「鬼佬」,我也會很喜歡如意的角色,神秘的鴉片,有毒而提神;主僕的感情,隱晦而迷離。如意是百無禁忌,百毒不侵的「怪人」,表面有著樸素傳統的打扮,內裡卻有禁不住的歪想與慾念,而自她出生以來,一直沒有人對她承諾過什麼,她在龐府中做傀儡,被退了婚約、被忠良騙了及遺棄,以及她被忠良拒絕回答的終身問題,一直以來也是沒有人對她負上什麼責任,直至最後她被端午出賣,告知她的未婚夫曾與她有染,如意這個註定悲劇的人物,最後也不再是什麼百毒不侵而「癱」了作終——這麼一個傳統女孩背後,可以有著這麼多可朔性的故事。
假如我是「鬼佬」,我更會很喜歡《風月》的故事背景,繁榮的夜上海,與傳統中國民初景色襯托下,使到《風月》能在中國的電影中「別樹一幟」;如意衫上的大紅花、龐府閣樓上的大燈籠、上海街道的大車,無一不是有效的告訴觀眾這些「反傳統」的感情與景況,正是發生在這些傳統中國社會與家庭裡。而陳凱歌很會利用這些鮮明討好的元素,去打開了外國觀眾的眼晴。在他的電影中,也有著中國人俗稱的宿命論,無論是如意般頑強,又或是忠良般不羈,角色最終的性格及結局,就是給自己「優點」所累的宿命;忠良的不羈,最後卻被不能再愛而成了大大口中的「廢人」;如意百毒不侵之身最後也被毒得癱了呆了,這些中國人彷彿註定悲哀的宿命,在陳凱歌花巧的構圖及劇情下,被映照出一種獨有的光影,而這種光影甚至令到華人觀眾本身也會感到陌生。
假如我是中國人,我會以為陳凱歌是一個外國導演,因為他漸漸脫離了中國第五代導演那種粗豪、激揚的情意,也沒有中國人艱苦生命的那種宣洩;從開首詩般畫意的荷花遊,到尾段刻意重播忠良、如意及端午孩提時在祠堂追逐的回望,也都表現出《風月》是西方的風,外國的月。
1996-06-00
電影雙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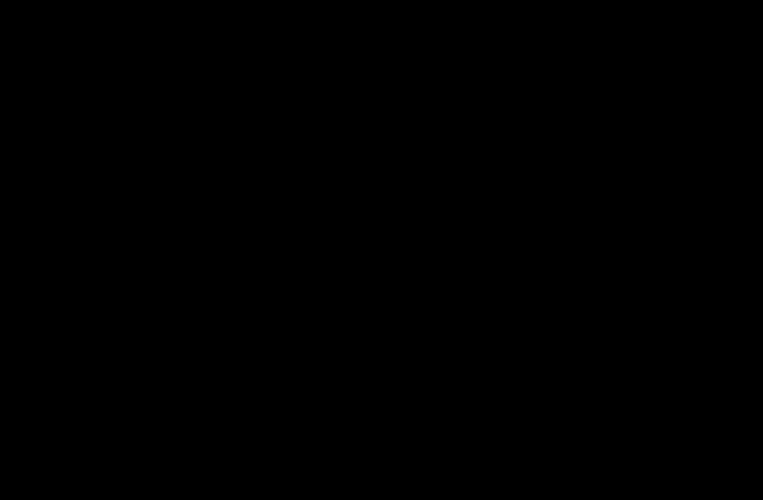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