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我可能是個悲觀主義者
2005-05-00
文:李元
四月一日愚人節那天,從網上和電視裏同時獲知張國榮自殺的驚人消息。一個鮮活的生命,藏著千頭萬緒的苦惱和怨恨,和那具血肉模糊的軀體,一同永遠地消失了……
當心緒平靜下來,我查找珍藏多年的那些採訪筆記,細細回味之後,一些似乎隱秘地、卻時時暗示人的答案,從朦朧中漸漸清晰起來,仿佛洶湧的波濤平息之時,你屏息靜氣地,可以聽見一聲微弱的叫喊,那麼輕的,但很固執、很深沉……
|
|
九年前,一九九四年九月十日,我受《電影故事》主編的委託,和同行驅車前往江蘇同裏,實地採訪陳凱歌導演的影片《風月》。傍晚,在同裏最大的私家花園退思院一個小樓的涼亭裏,我和張國榮談了近兩個小時。
「張先生,今天除了談談電影,我最想跟你聊的是男人,女人,愛和感情這個話題,好嗎?」
「男人,女人?」他聽後顯得有些突然,也有點感興趣,「這倒是個可以聊聊的話題。」也許記者大多會暴露採訪的功利性,太直逼目標,而我的閒暇姿態反而使他卸下警戒。這次採訪採取了閒聊的方式,其後他所傾訴的是盤繞在我腦海最深的音符。現在只要一靜下來,想起往事,總是驚奇自己曾在無意間問過一個人深藏在內心的東西,只遺憾當時沒注意……
「男人和女人的愛是非常不同的。女人跟男人結了婚,她的愛就常常會情不自禁,或者是不由自主的變得非常自私。比如男人在外面對另外一個女人有點好感,也根本沒什麼企圖,可是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會變得對男人不可容忍起來。這是我看得太多的事,小時候看多了,年輕時周圍朋友都有這種遭遇,所以我覺得男女之愛雖然很熱烈,但也很殘酷,因為人們總是學不會寬容,往往在愛的激情過去後,人會很無奈。有時只好得過且過,故意麻痹,緬懷那段激情,在回憶中求得平衡,其實感情早已淡漠了。所以男女之愛在我理解是一種一瞬那的火花,很容易消失,很難保存最初的感覺。男人和男人之間我認為不是這樣。男人們之間的感情比較寬容和溫馨,有一種堅實的依託感。」
也許因為我沒有太多採訪任務觀點,也許我是個上了年紀的平凡女人,當時他對我說得非常坦白。 |
「現代人對愛的理解更加個人化,更加有各自需求,有時候是害怕閑得無聊,不甘寂寞去尋找刺激而已。我演了很多角色。每個對愛的表現都不太一樣,不過他們有時都會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瘋狂性,捨命追求,結果追到的都是空的,或者跟自己原來想的相反,他們就變得很空虛,很絕望。我自己也常常有這種精神狀態。比如我賺了一些錢,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換房子,這大概就是現代人喜新厭舊的脾氣吧。買了一處房子,我自己忙著做設計,畫圖紙,逛店家,購傢俱,佈置房間,甚至裝修游泳池,花園,這個過程是最叫你興奮的,像是一種享受,全弄好了請朋友來玩,大家說『好,真好』。這時我的心情法反而很奇怪,除了滿足,還有一種空虛,新的空虛。怎麼啦?做完了,那下面去尋找什麼?所以常常住了兩年就會有一種膩歪,自己一直跟自己過不去,人家說你活得真累,可我覺得人生就是一直在尋找,一直在做夢,一個長長的夢。」
這年的11月份,和平飯店,我再一次採訪正在拍《風月》在外灘一部分戲的張國榮。這天我們仍舊聊了許多戲外的話。
「張先生,你總說人生是個夢,你好像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問。
「很可能是,因為我從小的環境並不好,從藝後不是一帆風順的。你問世上什麼人對我好,我一時都想不起來,好像人人都在說你怎麼好你怎麼好,怎麼怎麼了不起,但真正不會扔棄我的,也就是母親,她生下我,我是她的一部分,她當然不會棄我。可是這個社會裏有各種人,都懷著個人的目的,需要。他如果對你好,那只是表像,背後是什麼很難說,所以人是容易受欺騙的。」
「那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麼?」
「是被人欺騙,被人愚弄。」
「那你對人生,對周圍人都要求完美,理想,萬一追求不到這個環境,跟你心中差距太大,那不是很失望了?」
「對,我想我可能會採取一種毀滅的辦法,就是把壞東西扔掉,寧可毀滅。」記得他很俏皮地說著,現在想起來,他真的是用人生來演戲,在戲中完善人生。後來在一年多之後,我又去過松江車墩外景地,兩次採訪正在拍《新上海灘》的張國榮和劉德華。記得劉先生周圍總有一大群追隨者,很多記者頻頻用照相機對準他,而張國榮卻躲在一邊,極少跟人說話。現在想來,他真的是一個很透明、很坦白,也很幼稚的大孩子,他學不會圓滑,不願多跟人周旋,他話不多,但只要肯說,我想這一定很真。我的腦海中久久浮現他娃娃臉上的笑容和很謙和溫軟的嗓音。我想他是誠實的,對自己,對別人,連死也一樣是很坦白的。
電影故事(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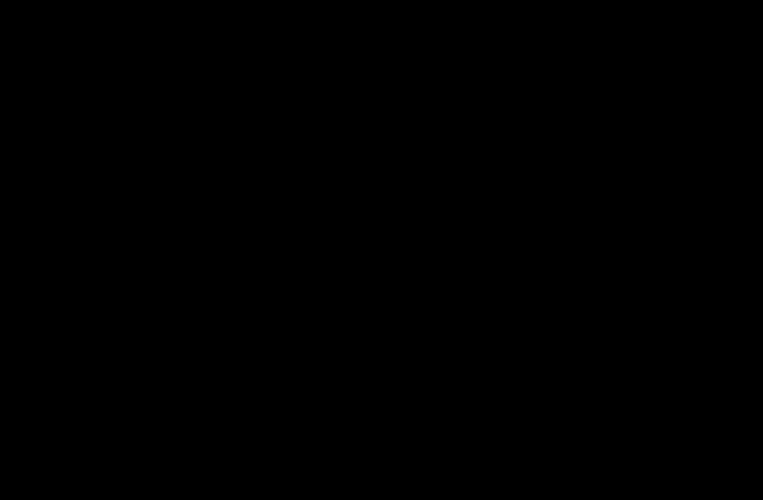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