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不完整的故事卻成立的電影經驗
文:焦雄屏
五、六十年代是個叛逆的年代。我想,每個在那時代成長的人,或多或少都對那段時間有些憶舊浪漫的情懷。流行文化對那個時代有最多的記錄:年輕人的叛逆,散發不盡的精力和壓抑,搖滾文化和衣著符號的興起,性啟蒙和性革命……充斥在音樂、電影、電視中。西方電影近年不遺餘力拍攝這類題材作品,像姜納森‧達米的《遊盪者》(Wanderers),大衛‧林區的《我心狂野》,柯波拉的《鬥魚》,甚至早期伊力‧卡山《天倫夢覺》都將叛逆青年視為某種反英雄典型。即使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也依樣畫葫蘆拍了不少《少年十五二十時》、《保鑣》、《死角》等,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叛逆作品。
然而,香港過往的青年叛逆電影電視,往往脫不了通俗戀愛或暴力械鬥的窠臼,直到王家衛的《阿飛正傳》展現著以往國片少見的感性(sensuous)氣息。特殊的場景、構圖、鏡位及鏡頭運動,角色的表演及動作姿態,使觀眾幾乎能清晰地感受到環境的氣味、溫度,以及角色內心難以平衡的激情。它既脫離港片一貫機械化的戲劇公式,也擺脫了台片寫實主義主導的靜觀美學。證諸台港電影工業界約定俗成的戲劇法則,導演王家衛的技法毋寧是大膽而犀利的,他不理世俗地一逕切入角色的內心世界,將空間、節奏轉化成角色情緒的註腳。
打從電影開始,觀眾便可探知王家衛的勇於創新。從來沒有建立鏡頭介紹時空,角色雄大的臉部特寫,不囿於傳統的鏡位及角度,省略及跳動式的對白,非有機式的戲劇段落安排,幾乎是對習於傳統電影觀眾的挑戰。然而,電影傳達出來的情緒卻異常準確,我想不出任何一部中國電影能夠如此清晰地針測出年輕人的不安、熱情、愛恨交織感情,以及人與人間那種明顯矛盾、無理性,欠缺規則的關係。占據在銀幕上受挫青年和他們的父母,似乎只有在白先勇等人早期小說中才找到相似的脈絡。現在小說中特殊的都市風情,人際恆常的相互折磨與羞辱,成長及性慾的壓抑與愉娛受傷,都經由非文字的視象呈現。它既不是通達的分析哲學,也不具寬廣的人文/藝術視野,但是,它血肉豐富(或血氣方剛)地描繪了一代青年的內心糾葛和心靈創傷。
《阿飛正傳》的剪接、結構和主體性也在國片中獨樹一格。從一個角色及其內心(片段出現他們的旁白),常自由地轉換至另一個角色。這種敍式處理,在法國的某些經典作,如《輪舞》(La Ronde)和《某夫人》(Madame de……)中也出現過,但在國片領域裡誠屬大膽。換句話說,王家衛拋棄了傳統觀眾對於主角的認定及敍事結構的因果有機性。電影中有些片段幾乎與戲劇性的發展無關,它成立純屬氣味性、感性,或角色個性的經營。也因為如此,斤斤計較「有沒有故事」、「故事完不完整」的觀眾,可能會緊張於尋不到劇情脈絡及答案而無法放鬆欣賞。
《阿飛正傳》當然沒有完整的敍事劇情。王家衛耗費了老板鄧光榮六十多萬呎底片,只拍出了《阿飛正傳》上集(梁朝偉在片尾首次出現數分鐘,節奏及場面調度純屬上乘,可是他是個什麼樣的角色,他身上會有什麼樣的故事,王家衛都無暇交代,就讓觀眾結束於訝然和荒謬的情緒中)。縱使如此,王家衛仍創下國片先例——一個完全沒有結尾卻成立的電影經驗。除了場面調度及導演個人色彩之外,《阿飛正傳》成功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演員的角色塑造。無論是張國榮充滿困擾的成長青年,或是劉嘉玲率性直爽的風塵女郎,或是張曼玉孤軍無助的售票小姐,甚至那位只說上海話的交際花母親潘廸華,都使段落式、疏離式的戲劇處理顯得趣味盎然。
《阿飛正傳》在香港的票房並不成功,但是,我們仍期望看到下集的出現。王家衛的做法在電影工業界可能不是受歡迎的人物,但是長期在公式化桎梏下的台灣電影界能出現《阿飛正傳》這樣的作品,至少像我這樣的觀眾是十分感激的。
1990-12-24
中時晚報(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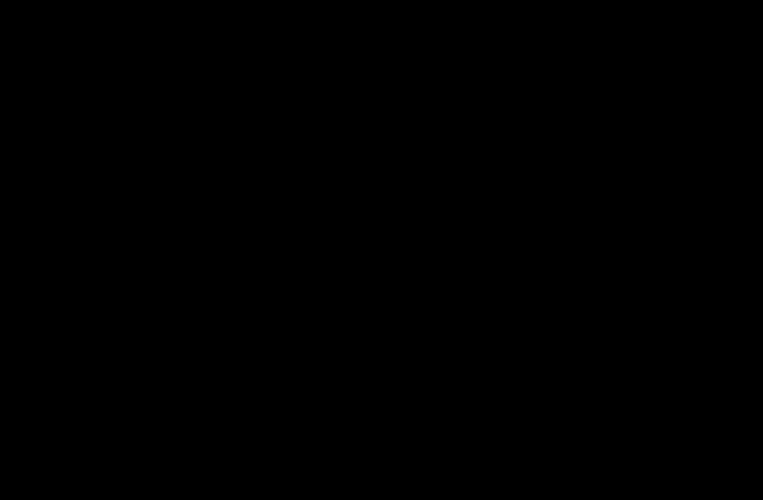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