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阿飛正傳:無可抗拒的宿命人生
文:小秋
一直以來,看王家衛的電影,就是圖他個迷人的情調,和那種難以言喻的感覺。說穿了,他不講什麼人生的大道理,也不談社會現狀、人情事理,他就是一股腦兒地描寫人面臨感情時的堅持、無奈、犧牲、自私......,在風花雪月的獨白中,嗅出那種熱到骨子裡的感動。
《阿飛正傳》找來一票大明星助陣,大手筆、大製作,竟拍出這樣一部引起爭議,但在時代的洪流中蔚為經典的電影。它一反常態的敘事手法和影像,對觀眾是一種新的刺激和挑戰。就談開場好了,一開場就是特寫,張國榮浪漫到死的文藝腔對白,就已經揭示了王家衛欲以本片建構一種全新的電影語言。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跟我在一起。我會記得這一分鐘。這是一個事實,我們改變不了——因為已經過去了。」《阿》的故事於六十年代發生,片中古樸時鐘的大特寫,象徵感情受歲月磨損而逐漸消逝的殘酷事實。張國榮「我會永遠記住這一分鐘」的承諾,充滿著天長地久戀曲的浪漫意境,但卻道出男性為了討好其心儀的女子而變得虛偽浮薄的可悲情狀。全片後段張國榮沒有為感情作出犧牲,只讓自己的生命孤獨地離去,從前承擔感情所表述的一言一語,終由濃烈而值得細想的真心話化為蒼白而虛假的謊言。
電影中更有無足鳥的比喻讓人印象深刻:「有一種小鳥生下來就沒有腳,它們一生都在飛翔,無法著地,它們一生中唯一著地的一次就是它們死亡的時候」。
《阿》內張國榮不願意對感情持專一的態度,在複雜難控的愛情世界內四處遊離,以玩樂的輕率心理對待任何一段與劉嘉玲、張曼玉隨意開展的感情。他在影片內對男女間離離合合的瀟灑自若,仿佛訴說典型阿飛是一隻不落地小鳥的不變定理;張曼玉和劉嘉玲對阿飛的盲目傾慕與迷戀,仿佛訴說一個又一個女人的悲慘故事。張與劉的付出與其收獲不成正比,灌注百分之一百的感情卻得不到百分之五十的回報,這證明愛情不能以傳統的數學公式計算,它是一場男女全力以赴卻慘冒粉身碎骨危機的鐵人拉力賽。
《阿飛正傳》不少鏡頭刻意經營出那時候港片少有的迷人感性,滲出一種或多或少的戀舊情懷。還記得在影片的結尾,那火車外不斷掠過的叢叢綠樹之間,浮動著一份濃郁的憂傷。人生正是如此,人們自有人們的悲哀、幸福與絕望,我自有我的。不原看到孤獨,卻習慣孤獨。不願愛上別人,卻習慣被別人愛上。不願永遠的飛,卻沒有可駐足的心靈。
我知道有這樣一些人,只有當眼睛前面擋上墨鏡,耳朵裏面塞進耳機,踏在地上的腳步才會有力量。這樣的力量來自於拒絕,而所謂拒絕,其實不過是將自己可能的缺口都給堵上,比如耳朵,比如眼睛,這樣你就自足了,這樣也就有力了,這樣你就可以隨手甩出一些諸如“我不屬於任何森林任何土地任何人”的少年意氣然後很驕傲。
張國榮離開菲律賓生母家的那段鏡頭很漂亮,張國榮的腳步很灑脫,慢鏡頭配上話外音---張國榮的獨白:「我終於來到親生母親的家了,但是她不肯見我,傭人說她已經不住這裏了。當我離開這房子的時候,我知道身後有一雙眼睛盯著我,但我是一定不會回頭的。」說過不回頭了,慢鏡頭就轉成正常的速度,色彩亮起來,音樂聲起,腳步也就突然開始變得有力,「我只不過想見見她,看看她的樣子,既然她不給我機會,我也一定不會給她機會。」這時候你知道其實沒有機會的是那只鳥兒,它真的失去了活著下地的機會。
總以為王家衛想說的好像除了拒絕,還有錯失。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在拒絕,而是在錯失。拒絕的發生,或者是因為我更有自主性,或者是由於她更有自主性,反正是兩個人中的某一位所呈現的東西不符合另一個人的欲望或念頭,而錯失不然,錯失的原因只能怪罪時間、地點或者……還有命運。
這就是阿飛正傳,它給人的感覺要不就是你看了二十分鐘因如同嚼蠟,不知所名,而拒絕看下去;要不然就是徹徹底底地愛上它.。所以在票房上,它集結香港幾乎所有巨星仍然慘敗。在藝術上,它是華影界的劃時代的一面旗幟,從此王氏的虛無主義,無根藝術,逐漸走向成熟,逐漸大行其道。
整個影片在頹廢的六十年代氣息裏探討時間與宿命之間微妙的關係,含義深遠而又不著痕跡。張國榮的表演魅力無窮,攝影優雅從容,轉身離去的那個跳減慢鏡讓人至今難忘,也許,這就是阿飛。至少,這就是張國榮給觀眾留下的那個最難忘懷的阿飛。
參考資料:焦雄屏。台港電影中的作者與類型。遠流出版。
1991-00-00
台灣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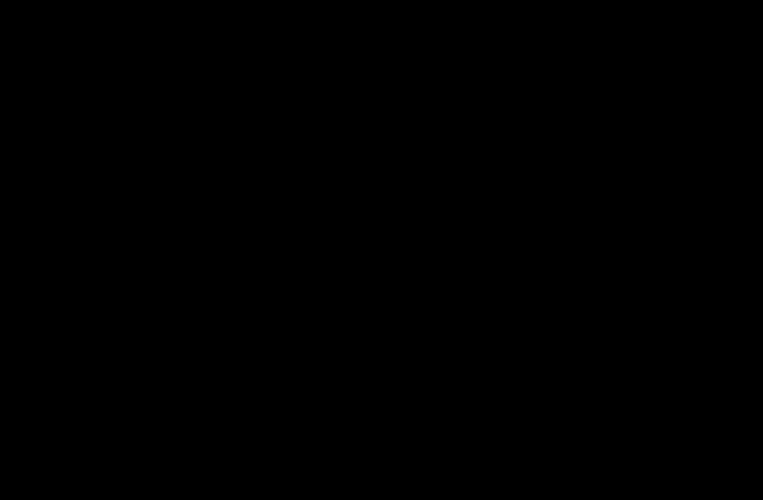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