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後榮迷」與「後榮論述 」
2013-04-15
文:潘國靈 (靈感國度專欄)
連續幾個星期以來,電影、音樂會、演奏會等不斷在「懷念哥哥」,真是「停不了的張國榮」,我因膽小一直不敢看的《異度空間》,也禁不住在大氣電波看了。坊間出現「後榮迷」這詞彙,來指稱在張國榮死後才認識或喜歡上這歌影者的年輕人,我的「九十後」學生中就有不少,看來「後榮迷」還會不斷延續。
其實伴隨「後榮迷」這十年的出現,還有「後榮論述」的生產和建構。一個演藝者無論多麼紅、多麼「萬千寵愛在一身」,單有「人氣」不足以成為藝術icon;張國榮從流行文化巨星躍上「藝術家」的台階,除了他本人踏入九十年代後有意識地告別偶像期而更趨成熟之外,一個不容低估的事實是,文化評論上關於他的論述,自他死後不斷增生鞏固,這恰是其他辭世巨星,如陳百強、羅文、梅艷芳,以至鄧麗君等所不能及的。
 |
|
於張國榮的論著,這裏隨便舉例,在他死後旋即出現的,內地有北京出版的《再見,哥哥》、台灣有其遺作《異度空間》的電影劇本集、香港有電影雙周刊出版的《星河.星殞──銀幕上的張國榮》,且不提當年其他打鐵趁熱的紀念集、樂譜等。在香港,「戲迷學者」洛楓的《禁色的蝴蝶》將張國榮的演藝生命帶上另一學術研究的台階。今年張國榮逝世十周年,坊間又見新著如《霸王別姬賞析珍藏本》、《不一樣的煙火──張國榮音樂傳奇》、《張國榮音樂人生》等,不一而足。這裏說的還只是文字論述,未包括其他重塑張國榮及其時代的電影、歌曲等。
演藝者作為「文本」,固然得力於其本人有自身的文化底蘊,但論述作為「從後而來」的書寫,也反過來豐富和開拓了演藝者的「文本厚度」,成為語言、論述與權力互為形構的展示。很難找到像張國榮一樣的巨星,可與當代文化論述作如此多方面的契合。首先是他的「死亡戲碼」,有人甚至以「行為藝術」來稱之,儘管這有美化憂鬱、自殺之嫌,但撇開倫理眼光,憂鬱、失落與藝術家形象,素來有不解之緣,張國榮於此並非單一例子,以至其流星殞落,可說加入了「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They died too Young」的星河行列。加上他本人的俊美、Ego之大、坦言自戀的性格,又令人想到「水仙花」的形象,成為美學上和精神病學上,有關憂鬱、自戀與藝術關係的絕佳個案。「藝術性」以後,巧合或不,他死亡的戲劇性在香港亦添了特殊的社會意義,他選擇在「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從高處躍下,從此其死亡與零三沙士的集體回憶牢牢纏結,緊密相連。
十年回眸,零三年四月一日彷彿成為「凝固的一刻」,但張國榮同時也是橫跨三個紀元的。如今「八十年代」成為黃金歲月、多元並存、創意能量迸發的象徵,任何「八十年代」的文化論述亦繞不過「張國榮」這個名字。告別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電影事業上他遇上了出色的作者導演如王家衛、陳凱歌、陳可辛等,他本人作為「本色演員」,亦逐漸脫離偶像派而躍至「作者演員」的層次。在歌唱事業上,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加盟滾石唱片公司至後期轉投環球唱片,林夕給他度身訂造的歌詞如《紅》、《左右手》、《我》等,亦替他在音樂上找到更具個性的主體聲音。電影和舞台上他的「雌雄同體」表現,他本人的性取向和「出櫃」,與當今文化研究的多元性別、酷兒理論又極可唱和。「後榮論述」把以上一一接收、提昇、轉化,「後榮迷」所認識的張國榮,不是幾經波折轉型蛻變臻於化境,而是一則經時空壓縮、高度論述化的神話,不僅止於「哥哥」自身。
頭條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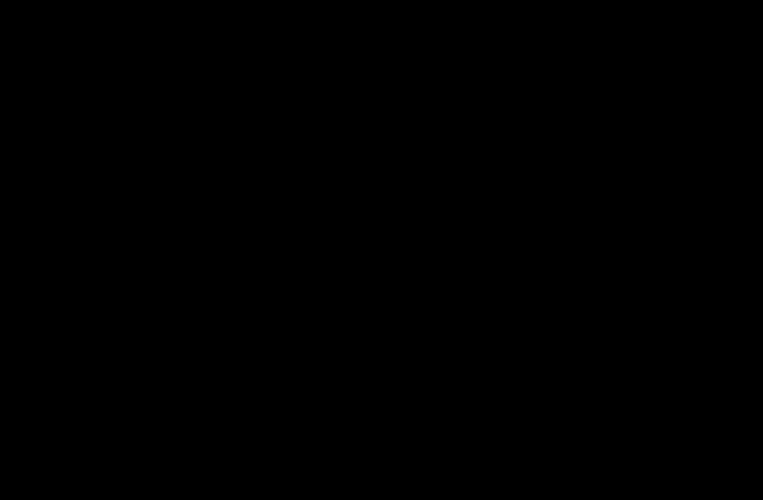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LeslieCheungCyberworld © 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